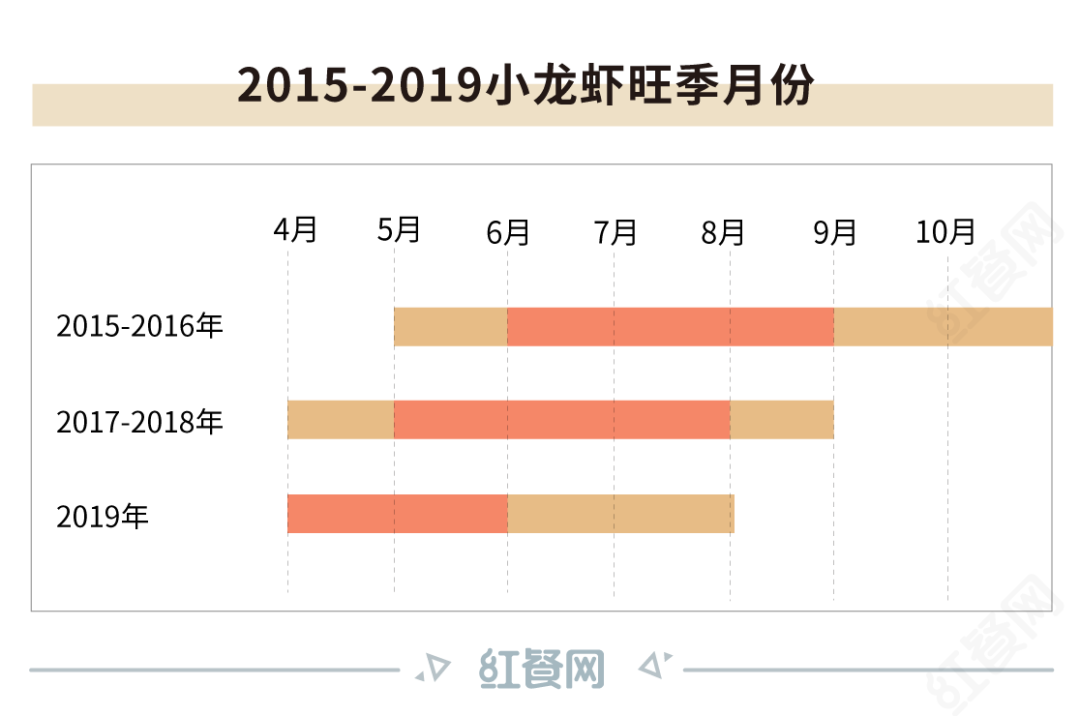在国内研究小龙虾化石的专家不多,而着名古生物学家沈炎彬先生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沈炎彬先生是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目前已经退休。
1988年3月20日,沈炎彬先生参加了中国第四次南极考察队,在乔治王岛进行地层古生物考察后归来。在4个月考察中,他采得大量孢粉、树叶、木化石、鸟类足印等标本。这是中国首次在南极开展这一学科的研究。
南京古生物学家沈炎彬向笔者展示小龙虾化石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成立于1951年5月7日,所长李四光,代理所长斯行健,赵金科、卢衍豪为副所长。其前身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及前中央地质调查所等机构的古生物室(组),1959年4月,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1971年3月,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主要从事古无嵴椎动物学、古植物学、地层学、沉积学、分子古生物学等基础理论研究。
1987年11月至1988年3月,沈炎彬随中国第四次科考队赴南极科考,在长城站附近进行远古化石寻找和古地层研究。对于这些搞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南极意味着天大的诱惑。在这块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大陆下,有太多远古地球的秘密等待发掘。
1984年11月20日,中国首次派出考察队赴南极考察,至1987年,中国先后派出3批考察队赴南极考察。由于第1次至第3次中国南极科考队的主要任务是建站,科考任务并不多,留给考察的时间也相对有限。为了最大程度利用在南极的时间科考,古生物所在中国南极科考队第四次科考前,特地向极地考察办公室提出了在南极进行地层与古生物调查的研究申请,因为这个项目的重要性,很快获得了批准。
南极科考工作是很艰苦的,科考队员每次外出科考,都是胶皮靴、厚厚的羽绒服打底,背上工具行囊就有十多公斤。南极的寒冷是因为它的纬度低,即便是夏季也常见暴风雪,夜晚的最低温度常常降到零下。在他们科考的三个月夏季,南极的白天特别长,有20个小时左右,而夜晚只有4个小时。对于南极科考生活的辛苦,沈炎彬回忆说,寒冷、危险都是早就料想到的,最难耐的是寂寞,三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只能见到相同的十几张脸,因此,没什么事情比收到家人朋友的一封来信、听到亲人声音更令人盼望和高兴了。不过,这看似最平常的愿望在南极却并不太容易实现,在上世纪80年代时,通讯远不如现在发达,那时的电信设备还是用的熊猫厂的无线电通讯,而且信号也不是很清楚,每天通讯的时间大约只有两三个小时清晰,而南极站的电话为了保证正常的工作联系是不可以随便拨打私人电话的,家属也不可能随便把电话拨到南极。正常的程序是,家人先和北京海洋局预约,然后批准同意后,再由海洋局通知科考队员通话时间,到时大家就等在话机旁边守电话。据沈炎彬回忆,科考队员守在电话机旁排队打电话算得上是南极科考队的一景,许多队员听说家人要来电话,常常激动得几个晚上也睡不好觉。
在南极的三个多月科考任务中,由于天气的关系,能够外出采集化石的机会不超过一个月,科考人员就趁着老天爷赏脸的机会玩命工作。沈炎彬在一个夏季考察结束,自己在乔治王岛和菲尔德斯半岛及纳尔逊北岸约40公里范围内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地层古生物调查,共找到11处化石产地,找到了大量的白垩世至早第三纪孢粉、植物叶、木材、鸟类足迹化石以及淡水硅藻、有孔虫、海生双壳类、介形类化石千余块,有109个属、212种,其中2个新属、48个品种是首次在南极发现。在整个南极科考期间,沈炎彬他们发现了成百上千块化石,这些化石,他们一块也舍不得丢弃。可是把这些化石带回来却是个难题,常常让科考队员费尽心力。因为每个科考队员能带回国内的行李都限重,最后,自己是缩减了部分行李,才将珍贵的化石贴身带回国内的。另一批化石实在带不走的,也是寄存在了长城站,等第二年南极科考时托人带回来,所有的化石全数运抵南京的时候,有整整十箱。
南京古生物学家沈炎彬(前排左二)
今天的南极大陆95%被冰层覆盖,仅存的植物只有苔藓和地衣等低等植物。但古生物学家沈炎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南极科考时,在乔治王岛的化石山发现了大量存在于四五千万年前(始新世)的古生物化石。其中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沈氏密锥蕨化石”尤为珍贵。生物化石的证据显示,亿万年前,南极的极地风貌与今天不同,那时南极是一片潮湿、温暖的地带,那里长着高大的树木、森林,沈炎彬还曾推断,当时南极半岛和南美南部存在着一条类似巴拿马地峡连接带。沈炎彬在南极长城站附近发现了多种南极古老落叶植物的化石遗骸、许多石羊齿、假山毛榉的树叶化石,各种各样的蕨类树叶,甚至还在附近发现了一截粗壮的树桩化石。在沈炎彬发现的树叶和树木化石中,假山毛榉的树叶比较宽大,脉络也非常清晰。树叶的形态、大小是判断它的生产情况最好的依据,通过树叶化石可以推断,当时南极曾经生长过非常粗壮的大树。
此外,丰富的蕨类物种,也是南极大陆曾经温暖潮湿的最好证据。南极曾经温暖潮湿,表明南极在远古是绝对不会在现在的极地位置,古地层的证据表明,在晚白垩世至早第三纪始新世时,南美南端与南极半岛间很可能有一条不规则的、狭窄的连续陆地相连,其古地理特征与现代连接南美、北美洲的巴拿马地峡十分相似。沈炎彬的南极科考填补了我国南极古生物学的空白,得益于此,沈炎彬还出版了中国首部研究南极地区的地层古生物的论着。此后,沈炎彬花费数年时间,在中国科考专家和国外科考专家的基础上,绘制了详尽的南极洲地质图,比例尺为(1:500万)。1994年10月,沈炎彬第二次踏上南极土地,探讨了生物地理区系、古气候类型以及冈瓦纳古陆拼合等一系列科学问题,为揭开南极地质发展之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沈炎彬研究员对于小龙虾化石的研究具有开创性,通过对于热河生物群的小龙虾化石研究,他认为热河生物群出土的奇异环足虾化石是现生小龙虾的祖先,现生小龙虾作为外来物种虽然来自北美,但是作为地球生命的一个分子,它在中国早就存在,只不过由于地质的变迁和火山爆发小龙虾迁移到北美。他对小龙虾的研究成果誉满海内外,得到了古生物学界的广泛认同。
沈炎彬的小龙虾化石研究成果:
Schram F R,沈炎彬.珍贵的小龙虾蜕皮化石.古生物学报,2000,39(3):416~418
Shen Y B, Schram F R, Taylor R S.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infossil crayfish of the Jehol Biota,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nd itstaxonomicdiscrimination. Chin Sci Bull, 2001,46(1):26~33
Shen Y B, Taylor R S, Schram F R. A new spelaeogriphacean(Crustacea: Peracarida ) from the Upper Jurassic of China.ContribZool,1998,68(1):19~35
Taylor R S, Schram F R, Shen Y B. A new crayfish Family(Decapoda: Astacida) from the Upper Jurassic of China, with areinterpretationof other Chinese crayfish taxa. Paleont Res, 1999, 3(2): 121-136
vanStraelen V. On fossil freshwater crayfish from easternMongolia. Bull GeolSoc Chin, 1928, 7: 133-138
沈炎彬,Schram F R,Taylor R S.热河生物群四节辽宁洞虾及其古生态.Palaeoworld,1999(11):175-187
沈炎彬,SchramFR,TaylorRS.辽宁热河生物群小龙虾化石形态特征及分类之甄别.科学通报,2000,45(18):1928-1935